本報特訊
五四意識型態的百年反思
本文題為〈五四意識型態的百年反思〉。本文將從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一生思想的轉折作為切入點,反思「五四意識型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本文的主要論點是:中國文化系統源自於《易經》,西方文化則是源自於《聖經》和希臘哲學,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五四時期主張「全盤西化」或「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系統其實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很容易陷入「雙重邊緣化」的危機。港台新儒家雖然盡心竭力想要維護中華文化傳統,如果未能妥善把握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分際,仍然可能使新儒家第三期的擴展遇到瓶頸,而難以為繼。
本文將以胡適和傅斯年作為「全盤西化」或「現代化」派的代表;以牟宗三和劉述先作為港台新儒家的代表,說明以上論點。基於此一前提,本文主張:破解「雙重邊緣化」困境,建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上策是:對於中國文化系統,最少要能把握儒家「道統」的「演化系譜」;對於西方文化傳統,則必須要能夠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2019新冠疫情爆發後,我集中心力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書系,其目的即在於幫助華人學者,掌握這兩種文化系統。
一、 費孝通的世紀反思
費孝通(1910-2005)是江蘇吳江人,也是最早揚名於國際的第一代華人社會學家。他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念,用以描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費孝通,1948)。他認為: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們的社會組織將他們綁在一起,成為一捆捆的木柴。中國社會的結構好像是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紋發生聯繫。這個像蜘蛛網的網絡,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這個富於伸縮性的網絡,隨時隨地都是以「自己」作為中心,這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是一切價值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
封鎖民族的「知識牢獄」?
費氏有關「差序格局」的概念雖然指出了中西文明的根本差異,而經常為華人社會學家所引用,究其本質不過是一種比喻而已,並不是「含攝文化的理論」。它反映出十九世紀末期,西方人類學者對於非西方文化的基本心態。
費孝通早年到英國留學時,受教於著名的波蘭裔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馬氏是功能學派的大師,要求學生進入田野從事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工作時,必須採取實證主義「主/客對立」的態度,考慮社會及文化建構具有滿足個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討文化理念的實質意義。
這種觀點跟另一位人類學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張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後者強調:必須考量社會建制跟整體社會運作之間的關係。馬林諾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許可以用來研究原始社會,但要用它來研究底蘊深厚的華人文化,就顯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費氏曾經被打入牛棚,不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費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協主席,在大陸致力於發展經濟的時代,他宣稱自己所作的學術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則一再強調中國社會學者必須要有「文化自覺」。
他逝世之後,周飛舟(2017:147)寫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轉向。1984年,費孝通寫過一篇〈武夷曲〉,稱自己對理學和朱子「自幼即沒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風味小吃〉中,費孝通還語帶諷刺地說:
試想程朱理學極盛時代,那種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間就毫不躊躇跨入金粉天地?……時過境遷,最高學府成了百貨商場。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在這裡受到了歷史的嘲笑。……我倒很願意當前的知識份子有機會的都去看一看,這個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費孝通,1989:p271-274)
1989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十年。在那個時代,費孝通還保有本書第一章所說的「五四意識形態」,認為「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是「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也因此為傳統書院改成「百貨商場」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對儒家文化傳統的態度,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社會學的「機制」和「結構」
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學反倒成為費孝通心中社會學擴展界限的關鍵:
理學堪稱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實際上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鑰匙。……理學的東西,說穿了就是直接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謂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我們今天的社會學,還沒有找到一種跟「理學進行交流的手段」。理學講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特殊的方法論的意義,它是通過人的深層心靈的感知和覺悟,直接獲得某些認識,這種認知方式,我們的祖先實踐了幾千年,但和今天人們的思想方法銜接,差不多失傳了。(費孝通,2003:p461-463)
費孝通早年受到「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迷信「實證主義」式的「科學主義」;改革開放後「復出」,仍然認為:儒家文化傳統是「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到了晚年,才清楚看出:儒家文化傳統的重要性,而呼籲中國知識份子要有「文化自覺」。他同時瞭解到:要找出中國社會運行的「機制」和「結構」,必須要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方法論」。
費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經指出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發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發展到宋明理學,確實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鑰匙」。理學所講的「關係論」,就是在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過程」,這就是中國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談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講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二、 朱子的未竟之志與西方的崛起
《四書》的正統地位
我們可以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明朱子發展理學並且以之作為基礎編注《四書》的重要意義。儒家經典,最早見於《莊子·天運》,孔子對老聃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這「六經」,是先秦儒家教學的材料,俗稱「六藝」。
西漢後期,其中《樂經》已經佚失,其他五種著作俗稱「五經」,立有「五經博士」,並收納弟子員。到了東漢,《後漢書》和《三國志》已經有「七經」的記載,但卻沒有說明其內容。唐代以《禮記》、《儀禮》、《周禮》取代《禮經》,並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列為《春秋》三傳,改「五經」為「九經」,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
到了宋代,宋太祖偃兵息武,重用讀書人,奠下儒學復興的契機。朱熹(1130-1200)是儒學第二期發展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在道教傳奇人物陳搏(872-989)《龍圖易》的影響之下,他綜合北宋四子對於大易哲學的「易理派」詮釋,以及邵雍(1012-1077)的「象數派」思想,而發展出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同時以之作為基礎,編訂《四書章句集注》。
當時的儒家經典以既有的九經,再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三經,其內容已經十分龐雜。《大學》和《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朱熹將之取出,又將《孟子》從「子」部取出,使其列於「經」部,跟《論語》一起合稱「四書」,並加以註釋。
宋亡於元之後,元仁宗(1825-1320)接受其儒師王約的「興科舉」的建議,於皇慶二年(1313)下詔,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所有參加科舉考試者的指定用書,並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作為漢人科舉考試增釋科目的指定用書,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良知理性」的分裂
任何人做一件事,必然有他的意圖,也可能有他自己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朱熹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調整,主要是因應外在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先秦儒學以《詩》、《書》及六藝教授弟子;漢代古今文經學側重「三綱五常」;到了魏晉南北朝,政治動盪,社會不安,佛、老盛行。魏晉清談源自易、老、莊三玄;隋唐佛學則是以譯經及自造的經典作為基礎。在這樣的時代衝擊之下,朱熹主張通過「道問學」的途徑,來達成「尊德性」的目標;希望通過「窮事物之理」,來尋求「理」的客觀準則,以建立「理學」,所以決定以「四書」取代「五經」,將先秦儒家思想打造成首尾一貫的「文化系統」,其重點則在於培養儒家的「士」。
然而,朱熹對於儒家經史的注釋,卻很難讓人以「文化系統」的整全方式,來理解儒家思想的內在理路。結果北宋以來,程朱一系的儒家學者試圖說清楚儒家的文化傳統,發展出以「道問學」作為中心的「理學」。陸王一系的儒者卻認為他們論述過於支離瑣碎,而主張「知行合一」,發展出以「尊德性」為主的「心學」,中國人對「良知理性」的理解,也從此分裂為二。
西方的崛起
在同一時期,西方文明也邁入快速發展的時代。古羅馬帝國是實施奴隸制的多神教國家,基督教原本是讓奴隸獲得「精神救贖」的宗教。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遷都君士坦丁堡。西元392年,迪奧多西一世訂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到了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羅馬。由於北方蠻族的不斷入侵,以及人民起義,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並分裂成許多封建王國。
西元第七世紀,阿拉伯人勢力崛起,佔領耶路撒冷。西元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東羅馬帝國覆滅將近一千年之間,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現代科學開始萌芽。到了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歐洲科學更是快速發展,伴隨著產業的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三、 反傳統的意識型態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全盤反傳統主義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越演越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72/1983)。
五四時期,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不瞭解歐洲啟蒙運動的根本精神,是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思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的宗教形上學,而用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跟著反《易經》的形上學,完全不瞭解《易經》和《聖經》在中、西文化系統的重要位置。當時主張「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以錢玄同為首,掀起了一陣「疑古」的風潮。在「科學主義」風行的時代氛圍裡,他自稱「疑古玄同」,對於史書上的記載都要抱持懷疑的態度,細加考究,更不要談史前的傳說。當時主張「全盤西化論」還發生了一則著名的故事:
胡適「截斷眾流」
胡適(1891-1962)是安徽績溪人,14歲進澄衷學堂。翌年考取中國公學。兩年後,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五年後,改入哥倫比亞哲學系,師從於主張「實用主義」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1917年九月,27歲的胡適由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胡適留洋七年,又是哲學大師杜威的高足,講授西洋學問,沒人敢說甚麼,但是他教中國哲學情況就不一樣了。
胡適回國後,用了一年的工夫,將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改寫成《中國哲學史》上卷,但是這本書的下卷,卻是終其一生,未見完成。
以這樣的背景視域講中國哲學,當然會引起北大學生的非議。在他之前,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教師是陳漢章。他有「兩足書櫃」之稱,上課時通常是引經據典,從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一路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在講他的《中國哲學史》(卷上)的時候,卻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將遠古時期「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紀載,一律摒棄不談。在開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中,以《詩經》作為說明材料,從西周覆滅前的周宣王講起。
傅斯年仗義相助
如此一來,號稱有五千年的中國史就給截掉了一半。消息傳出後,許多師生斥之為「胡說」,有些態度激烈的學生甚至鼓動鬧事,準備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走。當時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有人邀請他一起前往聽課,傅斯年在課堂上幾次向胡適發問,而認可了胡適的回答,風潮才逐漸平息。後來胡適回憶這段經過:
「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絞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歷史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作品集》,第25卷,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出版)
傅斯年(1896-1950)是山東聊城人,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傅氏身材魁梧,性格豪放,有領袖氣質,這件事過後,與胡適成為莫逆之交。
然而,傅斯年之所以出面支持胡適,是受到當時學術風潮的影響,並不是他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真知灼見。當時中國學術盛行的是以「實證主義」做為中心思想的「科學主義」(Kwok, 1965)。胡適到美國師從杜威的「實驗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所謂的科學精神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一切都要「拿證據來」,拿不出證據來,就是「不科學」的,就不值一提。傅斯年判斷:「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得這一條路是對的」,所以傅斯年決定出面,「仗義相挺」。「這一條路」就是「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道路。可是,「這一條路」也讓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寫不出下冊,不能對中國哲學系統的「知識型」作出完整的論述。
反形上學的風潮
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隨著「科學主義」旋風而掀起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把「五常」當作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把它們等同於西方啟蒙時期所排斥的「形而上學」概念,應當一律予以拒斥。舉例言之,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在「五四運動」爆發後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遊學。在六年半的時間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1926年十月,傅斯年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國,並接受中山大學之聘,於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他積極籌畫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舊以該所籌備處的名義撰寫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確指出:「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疇,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證是歷史方法之大成。」而依此而提出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三個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做研究時應用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竟如斗室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
「仁義禮智」的機制
在三條標準中,傅氏特別強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最後,傅斯年振臂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從傅氏鎖定的三個標準以及他所強調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已經可以看出:傅氏是個極端的「實證主義者」。歷史學和語言學是否可能「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是個最值得嚴肅探究的問題。依照本書的分析,孟子的「仁義禮智」或「五常」,是儒家社會中的人際互動最重要的「機制」。如果歷史學和語言學硬要將之排除在外,史語所怎麼可能建立「科學的中方學之正統」?
四、 港台新儒家的奮鬥及其侷限
五四狂飆過後,上節所述是「全盤西化派」或「現代化派」對待儒家文化傳統的基本態度。在這種情勢下,鍥而不捨地想挽救「花萬飄零」之儒家傳統者,唯有港台新儒家而已。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新儒家的核心人物牟宗三(1988)認為:對於形塑中國人「普遍的精神實體」而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儒家文化傳統,他將儒學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大時代:(1)先秦儒學:以孔、孟、荀為代表;(2)宋明理學: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3)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
牟宗三的判教
牟宗三憑個人堅定之意志,獨力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翻譯成中文,又以之作為基礎,梳理宋明理學的發展,撰成三巨冊《心體與性體》(牟宗三,1968-69),一生的學術貢獻確實是如他自己晚年所說的「古今無倆」。
在《心體與性體》一書中,牟宗三(1968)反覆指出:
「朱子後來所謂『太極只是理』,或『性只是理』乃是所謂『但理』。動靜闔闢是氣,心與神亦屬於氣。理氣雖不離,亦不雜。」,「將其所理解之性體、道體、仁體(都只是理)著落於致知格物之言之。」(頁18)
「其言致知格物只成為散列之『順取』,而只落實於存有之理之靜攝。」(頁527)
他將朱子的進學之路歸諸於其「家學與師承」:
「其家學與師承俱以《大學》、《中庸》為首出也。」(頁1)
「朱子因膠著於大學,卻擰轉而為橫列的靜涵靜攝之系統;主觀地說,是認知的靜涵靜攝系統,客觀地說,是本體論的存有之系統。」(頁54)
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之「理」,乃是「存在之理」,它跟西方哲學的「形構之理」本質並不同。不僅如此,中國哲學中的「存在之理」亦有兩種。一是動態的「存在之理」;一是靜態的「存在之理」。兩者和「形構之理」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是「超越的」;但是在是否能「活動」(創生)方面,兩者卻有所不同。他將前者稱為「即存有即活動」的本體;而將後者稱為「只存有而不活動」的本體。
「存在之理」
依牟宗三的看法,在《孟子》以及《中庸》、《易傳》中,先秦儒家所談的道體、性體是屬於前者,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的「存在之理」;程伊川與朱子所說的道體、性體則是屬於後者,是「只存在而不活動」靜態的「存在之理」。換句話說,伊川與朱子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新見解。於是,牟宗三將程伊川到朱子之系統,從「正宗儒家」、「宋明儒家之大宗」中排除,並視之為是正統儒家思想的歧出。
牟宗三認為:這兩者的差別,在於他們究竟是透過何種「工夫論」來掌握「存在之理」的。《孟子》、《中庸》、《易傳》的傳統儒家,採用「反身」的方法,追溯自己的本性(理),而來體證作為本體的「存在之理」。牟宗三稱之為「逆覺之路」。相對的,伊川、朱子卻是根據《大學》,採用「格物窮理」的方法,認為心外的萬事萬物各具有「理」,必須一件一件地認知各個外在事物之「理」,最後才能獲得惟一、超越、而絕對的「存在之理」,以貫串個別之理。這樣的方法,牟先生稱作為「順取之路」。
太極作為「存在之理」的性體或道體,本來具有創造道德或創生萬物之作用,它必須透過「逆覺體證」才能完全掌握。然而伊川、朱子卻採取「格物窮理」的認知方式,要求最後的「豁然貫通」,將「知識問題」與「道德問題」混雜,使得「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存在之理」。
牟宗三的偏誤
藉由「順取之路」雖然能夠建構出「橫攝系統」的客觀知識,但是卻背離了儒家正統的「逆覺體證」,跟王陽明「心學」的「縱貫系統」並不相同。所以他認為宋明理學中陸王一系是儒家的正統,程朱一系只能說是「別子為宗」。
在《宋明理學的問題與發展》一書中,牟宗三(2003)以「西哲化中哲」的方式,從各種不同的面向,討論「實現之理與形成之性的區別」(頁107-118),最後他說:
以上所說,暫綜結如下:宋儒所講道德性的天理、實理,當通到寂感真幾時,我們即名曰宇宙「實現之理」;而凡順定義一路所講的理,不管對這理是如何講法,是唯名論的,還是唯實論的,是經驗的、描述的,還是先天的、預定的,我們總名之曰邏輯的「形構之理」。(頁114)
「實現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又名「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它跟「形構之理」(principle of formation)之間的區分,對於瞭解中、西文明的差異,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必須在此細加析論。本書將中、西文化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國的文化系統源自於《易》經,西方文化系統源自於《聖經》和希臘神話,這兩種文化系統各有其「存在之理」與「形構之理」。牟氏說:宋明理學是一種「存在之理」,這是正確的。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並非沒有「形構之理」。
「中西會通四聖諦」書系的第一部《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很清楚地指出:道家解釋《易》經,早已發展出一種李約瑟所謂「有機論」的科學(organic science),跟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來的「機械論」科學(mechanic science)並不相同。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個不相干的議題,然而,牟宗三在他的大論述中沒有正視中、西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結果卻可能使港台新儒家蒙受無法繼續擴展之「苦」。
劉述先說「理」
另外一位「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學者劉述先(1934-2016)在《朱子哲學的發展與完成》一書中,從思想史的角度,回顧朱熹一生治學的歷程(劉述先,1982)。該書指出:朱子求學,從「未發工夫」入手,在「中和萬說」階段,經「己丑之悟」有了新的體會,而作「中和新說」。朱子先完成〈已發未發說〉一文,再修改成一篇精要的〈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朱子說:
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徳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己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荘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黙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審,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文集卷六十四)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朱子的嘔心瀝血之作。然而,朱子一生治學所要彰顯的儒家精神究竟是什麼?它對現代華人又有什麼意義?劉述先受到西方哲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影響,認為人必然會有某種終極的關懷(ultimate concern),他因此而對宋儒所提的「理一分殊」重新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在他看來,超越的「理一」,是貫通古今中外的,但它的表現則依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不能抹煞「分殊」層面的差異。譬如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陸王、以及當代新儒家,他們思想學說的建構與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均不相同,但都歸本於仁義,並注重對生生不已的天道和悲憫惻隱之仁心的體證。
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處理傳統與現代以及「中西會通」的問題上,他藉助《莊子。齊物論》上的說法「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將超越的「理一」和現實的「分殊」視為「兩行」,認為「兩行之理」是儒、釋、道的共法。西方哲學在「解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之後,應當也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這樣就可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解決中西會通的問題(姚才剛, 2014)。
這個觀點跟本書的立場並不相同。在我看來,儒、釋、道「一行」談的是「存在之理」;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另外「一行」則是在析論「形構之理」,兩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作為其「終極關懷」的「理」並不相同。這「兩行」分別代表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今天我們要談「中西會通」,必須弄清楚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形貌特色,不可將兩種混為一談。
五、結論:中西會通四聖諦
1992年二月,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反思研討會」上,余英時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知識份子邊緣化〉。在論及「知識份子與文化邊緣化」時,他說: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使他們可以理解。哲學家為了改變動中人的黑暗狀態,這時只有叫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著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國知識份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中國知識份子該如何破解這「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呢?。從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我回顧過去將近半世紀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得,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於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書系的第一本書,題為《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該書前半部的析論指出: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統的扭曲。這種「系統性的偏誤」很可能使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並使港台新儒家的發展承受難以為繼之「苦」。後半部則「對症下藥」,介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這本《牟宗三的科學觀》是「中西會通四聖諦:苦、集、滅、道」書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將重新組織並改寫第四版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每一章後面添加一節「文化反思」,說明該章在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應用。這是「集」,希望能夠匯集西方科學哲學之精華,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
2021年八月一日,最早提出中國知識份子「雙重邊緣化」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在睡夢辭世。他逝世之後,海內外一片哀悼之聲,大陸學術界稱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他是「買辦學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絲」,收藏了他的許多著作,當時覺得奇怪,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因此回頭仔細看他的著作,才發現余氏其實是本文所謂的「現代化派」,著作中潛藏的問題確實十分嚴重,所以陸續在香港《亞洲週刊》和《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的研究取向,將來準備出一本書,題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作為本書系第三部之一。希望華人學術界中「自我殖民」的陰魂能夠因此現身,而得以「滅」渡之。
第四部包含兩本書,一本是《玄奘與榮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這是我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依照我所發展的知識論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Hwang,2019),希望回應費孝通反思「五四意識型態」後所提出的「大哉問」,以便走出本土社會科學之「道」。
參考文獻
牟宗三(1968):《心體與性體(一)》。台北:正中書局。
牟宗三(1968):《心體與性體(二)》。台北:正中書局。
牟宗三(1969):《心體與性體(三)》。台北:正中書局。
牟宗三(1982):〈儒家學術之發展及其使命〉,《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臺灣學生書局,頁1-12。
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余英時(1975):〈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滙流〉。《歷史與思想》,頁1-46。
姚才剛(2014):〈「理一分殊」與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化-劉述先先生對傳統與現代問題的哲學省思〉。《鵝湖月刊》。第469期,頁4 – 10。
林毓生(1983):〈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思想與人物》,頁139-196。台北:聯經出版。
周飛舟(2017):〈「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37(4),143-187。
黃光國(2018):《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上海:觀察社。
劉述先(1982):《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灣:學生書局。
Hwang, K. K. (2019).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9(2), 67.
Kwok, D. W. Y.(郭穎頤)(1965/1987).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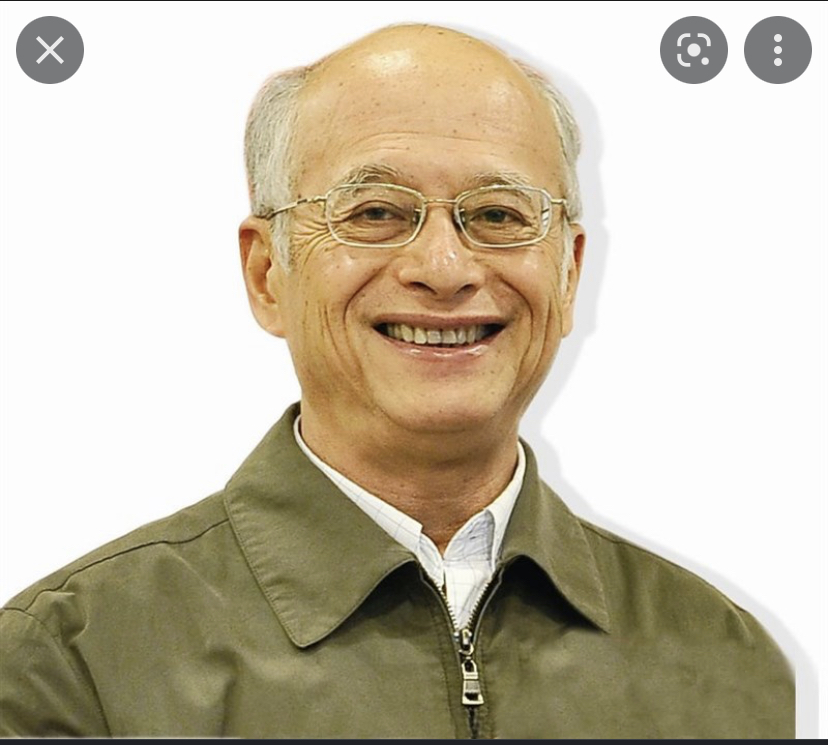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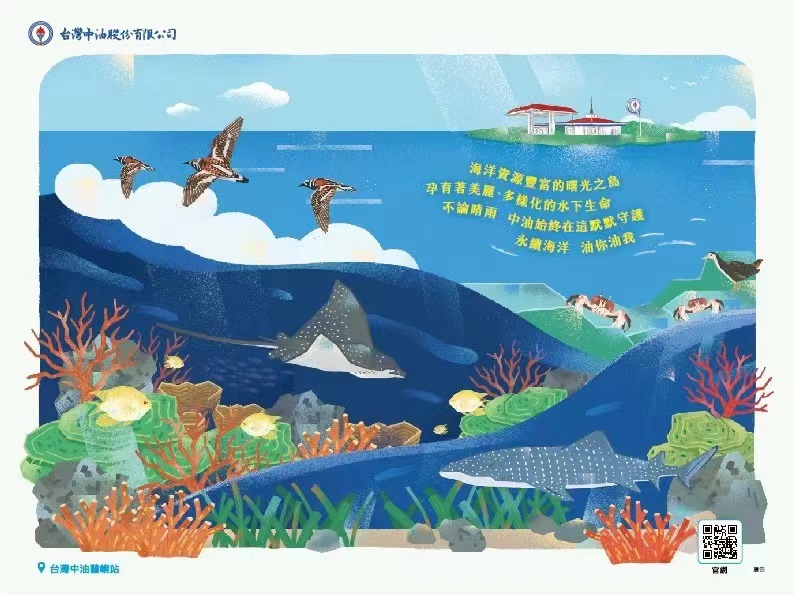
![衛福部[屏醫]升級急重症醫療 屏東國際醫療包機救援首例在屏醫@華夏新聞報](http://www.a14913.com/wp-content/uploads/2025/10/20251013a-衛福部屏東醫院強化急重症醫療05-768x432.jpg)
![衛福部屏東醫院中醫科治療顏面神經麻痺 [美顏針]助病患找回笑容@華夏新聞報](http://www.a14913.com/wp-content/uploads/2025/09/20250917a-屏東醫院中醫科治療顏面神經麻痺01-300x124.jpg)
![屏東醫院血液腫瘤科黃炯棠醫師2025.9/1提醒[血癌]早期症狀盡速就醫@華夏新聞報](http://www.a14913.com/wp-content/uploads/2025/09/20250901a-屏東醫院血液腫瘤科黃炯棠醫師提醒血癌早期症狀盡速就醫03-300x139.jpg)
![衛福部屏東醫院林秀惠護理長分享親身經歷[後縱膈腔腫瘤]治療@華夏新聞報](http://www.a14913.com/wp-content/uploads/2025/08/20250822a-屏東醫院林秀惠護理長後縱膈腔腫瘤治療分享01-300x154.jpg)
![衛福部屏東醫院泌尿科張哲維醫師2025.8/18分享[尿路結石]定期追蹤@華夏新聞報](http://www.a14913.com/wp-content/uploads/2025/08/20250818a-衛福部屏東醫院泌尿科張哲維醫師尿路結石定期追蹤02-300x187.jpg)




